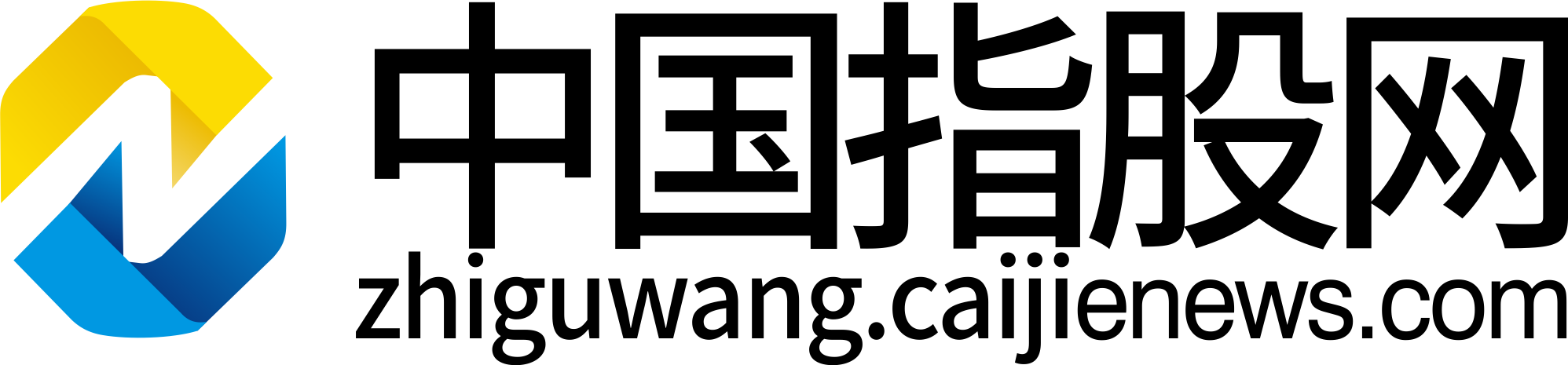
《将军令》三影 HE(伍)
(十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冬日天亮得晚,玄黑色的马车驶过玄正大街时,东方依旧一片昏暗的霾色,但眼看着正阳门便到了。
天斗朝寅刻点卯,天子脚下寸土寸金,住得远的朝官便受累些,唐三的镇北王府乃开朝高祖封赐,地段自然是好的,虽然这一代这位年轻的镇北王没怎么回来住过,但此时时影却是庆幸,好歹能让唐三多休息一会儿。
车架入了正阳门,在宫闱外的奉天门止步,这里是百官上朝府中车马停靠的地方,时影替唐三拢紧了滚边斗篷,看着他扬唇笑笑走下车架去。
虽然这已是众目睽睽的宫闱门口,皇帝还需依仗唐三击退外族,但唐三还是有些不放心时影的安全,想着百官点卯到底人多眼杂,时影又生得实在让人过目难忘,未免他这身份给时影带来不必要的危险,下车前他叮嘱了小医师,莫要跟他下去了,让时影先随着玉小刚回府。
说完,男人抖抖斗篷跨下马车,时影从厚车帘里挑开缝隙,定定看着唐三一步一脚印,款款走向如云的白玉阶,迈向这座王朝巍峨高耸的禁宫深处。
时影也没想到,老天爷如此儿戏,偏生是这一天,皇城下起了初雪。
瑞雪满京都,宫殿尽成银阙,这场飘摇的雪来得突然,轻鹅绒一般覆下大内的重重屋脊,奉天门外静了下来,时影并没有让玉小刚送他回去,而是就待在车架上坐着,不知为何,他不太想一个人回府,一想到这是唐三回京后第一次上朝,那人拖着病体磋磨半日,若是还只能一个人回家....光是这么想着,时影便止不住拧眉。
于是,问过玉小刚后,他便守在了车里,想要守着唐三下朝,若是那人有什么不舒服的,也可提早应对。
初雪来得毫无征兆,四下同样等候的朝臣仆从们多是走去正阳门外躲雪去了,见四下无人,时影撩开了一侧车帘,倚在唐三坐过的位置朝外望,目光远远瞧见了晨晓的一抹熹弱微光,折射在禁宫屋顶明黄的琉璃瓦上。
巍然殿宇从宫门顶端的缝隙里露出冰山一角,时影望见那飞扬的檐角屋脊,一整排鳞次排列的神兽雕饰精巧细致,是时影在九嶷山见不到的尊贵与华美,可他却只觉晃眼,某种莫名的窒息感让他一瞬几乎要呼吸不畅,时影攥拳的手指紧了紧,眯眯眼后垂下眼睫,望着宫闱青石路上渐积的薄雪,男人清俊淡然的眉眼里忧色愈显。
两个多时辰后,朝散,朝官们三三两两走出议政殿,各色长袖袍服的大人们三五聚众错落走出大内。
玉小刚方才被时影叫进了车架里取暖,当下也赶忙出来,立在马车前想要望一望自家王爷,时影在车上早已等得难耐,两个多时辰的早朝,还不知唐三到底情况如何了,他也想下车,却又想到了唐三的叮嘱,为怕打乱唐三的安排,给他添麻烦,时影忍住了冲动,还是坐回去侧榻上,靠在车窗边透着缝隙朝外看。
朝官们或许也是没想到外头竟飘起了雪,他们个个穿得都不够厚实,当下出了殿门便都被冻得哆嗦,三两两上了各自的马车便着急离去,不一会儿,奉天门外等候的车架便几乎走了个干净。
只不过,走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若有似无地瞄了眼宫门外那架通体玄黑的马车,他们都认出了镇北王府的徽纹,那是镇北王唐三的车架。
想起方才朝堂之上,继任镇北王后第一回上朝的年轻王爷,镇守北境、手握重兵的一方统帅,那人一点都不像是年方二十三,倒像是早已历尽千帆,哪怕是以此及冠之龄立于众武官最前端,唐三站在年迈的太尉身后,也丝毫不显势弱。
若不是看他面色苍白、唇无血色,还异于寻常朝官着了厚袄里衬、颀长纤瘦的模样,怕是群臣一时都忘了,此人已是缠绵病榻多年,是个天下皆知要命不久矣的病秧子。
北堂墨染一袭淡黄的皇子朝服走了出来,哪怕一脸漫不经心的姿态也显得矜贵优雅,但玉小刚却敏锐察觉,这位大皇子像是刻意放缓了步子,他远远与墨染幽邃的眼对上一瞬,心头一跳,视线赶忙朝北堂墨染身后望去。
人群的最尾端,面色苍白如纸的唐三围着滚边的长风斗篷,一步一脚印地自如云的白玉阶上徐步踏下。
他的身后,九天宫殿郁苍苍,紫金龙楼直署香。
那样俊挺纤瘦的一个人,满身浓墨重彩的墨色,薄雪白了肩头,染了眉眼,在这巍然恢弘的皇权至高处,他孤身一人,病骨支离,步履飘浮又笃定地徐徐朝外走。
四下终于无人,眼看着北堂墨染也上车离去,时影下了马车,抬眸第一眼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
天斗这一年初冬的第一场风雪里,时影打着一把伞,一袭白衣白斗篷俊逸出尘,谪仙一样的人俊华如松,身姿笔挺地立在寂寥的奉天门外,与漫天的绒雪几乎融为了一体。
吃人一样高耸的朱门,时影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他的病人步履逐渐错乱,俊脸沉得滴水。
唐三一眼便看到了那人,心尖一动,毫无血色的唇扬起一抹笑来。
眼下,蓝银蛊已逐渐陷入沉眠,不再压榨唐三身体生机的同时,却也再无法为他补充气血,哪怕只是一场初雪,也难免寒气袭人,唐三只觉当年箭伤的旧患处又是一阵熟悉的蚀疼,入了骨如蚁虫啮咬的酥麻阵痛,让他面色一白再白,若非时影昨夜早有预料为他施了两针,他怕是在议政殿便要失态了,更何况还要在朝堂上....
唐三走出奉天门,四下无人便终于松了口气,脚下一个踉跄被时影迎上来撑住手,他几乎大半个身子都靠进了时影的怀里,医仙公子眉眼冷冽,厚实的斗篷里却暖热得很,唐三明明自己也穿着厚袄,不知为何却就是觉得时影身上更暖些,不自觉倚着人蹭蹭。
时影没留意怀里人的动静,反手将伞递给了身后的玉小刚,他展臂揽住了唐三,将这人肩上落的一层薄雪扫去,赶忙搂着人塞进了马车里,玉小刚见状麻溜地封好门帘,回身便挥鞭驱马,火速驾车而去。
车架里暖炉不断,时影将唐三扶进了软靠深处,将备好的绒毯给他盖上,摸摸他冷寒刺骨的手,紧蹙的剑眉衬得整张俊脸都结了冰,但时影到底是唐三的医师,对眼下状况也不是没有预料,软榻上的小几早已被时影挪到一侧去,他矮身将唐三的长腿也架上车榻,自己倚在软靠边抱着人,用自己的体温给这人暖着,还不忘解下自己的斗篷又给唐三再加了一层。
俊容苍白的男人被暖热的体温拢着,脸色舒缓了下来,寒气逐渐褪去,旧患处的蚀疼也随之缓和了些,唐三习惯了疼痛,触感也迟钝,忍耐力比之常人要好得多,身体里有一阵没一阵的酥麻阵痛还未褪尽,他竟然也觉得舒服许多,头脑昏昏沉沉,眼前雾蒙蒙地看不清明。
周身的暖融让唐三几乎要昏睡过去,他能感觉到,身边若有似无的雪寒薇香近了又远,远了又近过来,待他努力抬眸看才发现,身上被人盖得厚实的同时,手里还多了个紫铜手炉,时影揽着他靠在厢板的软靠上,这人身上好闻的雪寒薇香让他紧促的心一下子平和下去,安宁得不像话,唐三勾唇笑笑,莫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些年来,他一直是镇北王府的支柱,是北境军的支柱,是北境的支柱,哪怕他病骨支离、再不能同他珍重的同袍兵士们一起冲锋陷阵,但他也始终尽自己所能地护佑着自己的身边人,自己的士兵,还有他所能挽救的每一寸天斗的国土。
唐三习惯了被人依靠,成为别人的主心骨,却没想到有一日,居然也有人能够给予他这样的一份安心感。
仿佛有时影在,他便不必再计算着自己到底还能活多少日,到底还需要坚持多久,还需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安排好哪些事情。
唐三看得通透,并非所有的医师都能给他这般的笃定,也不完全因为时影医术精绝、远非寻常医者,好似便是时影这个人本身,便能带给他完全不同于常人的心安,明明相识也不算久,这样的亲近感却来得热烈。
他的身份使然,本不该如此轻信于人,但或许也是在苦寒的北境坚守得太久了,他有生死与共的同袍,有英勇无畏的士兵,北堂墨染和言冰云碍于身份只能书信关怀,他确实是久未有妥帖亲近的友人在旁了。
【...朋友....吗?】
【朋友...也很好了吧?】
唐三唇角笑意淡了些,撑着手臂抬眸看了时影一眼,嗓音微哑:“我没事,就是没想到这么不凑巧,竟然下雪了啊。”
时影垂眸凉凉看了他一眼,抿唇不太想说话,触了触唐三的手,感觉到指尖回温,俊容面色这才好看了些,他手上抚过去握住男人的腕骨,牵着人搭在绒毯上,径自闭眼诊起了脉。
唐三另一手摸了摸鼻子,瑞凤眸里多了无奈的神光,心里暗想着不妙,他的小医仙好像真的有些恼了,他揉了揉额角,到底是有些心虚,但还是不能瞒着时影,抓上身后人揽他的臂肘,手握重兵的镇北王小心翼翼抬眸,轻轻拉了拉时影的袖摆。
“阿影,有件事,要和你说。”
时影松开了诊脉的手,俊脸上神色不变,大抵是昨夜两针垫了底,唐三气脉还算稳定,但一想到这人忍着旧患蚀疼在皇帝和群臣中强自支撑,为北境军出征的后方宁定、为边关安宁殚精竭虑,时影惯常淡然的心境便始终稳不下来,他知道唐三并未做错,也懂得他的坚持,却不知为何一看见这人扬唇笑,胸腔里就涨疼得厉害。
诊过脉才堪堪安心少许,但时影一听见唐三这么说,心里霎时又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眯了眯眼,终于还是叹了口气,有些认命的模样:“你说吧,何事?”
玄黑的马车碾过薄雪铺就的石板路,一路驶回了镇北王府。
(十五)
玉小刚和戴沐白都发现,自那日王爷下朝回来,时公子好似心情一直不太好。
时公子生得谪仙一样,医术高明不说,性情更是温雅随和,清冷而不失君子之风,整个镇北王府阖府上下,不仅是因他为王爷医治而感激他,更因这位确是灼灼其华、光风霁月的妙人,个个也十分尊敬他。
因而时影脸色难看了这么些天,不仅玉小刚等人发现了,连未央殿把守的昊天卫们、栖云殿打扫的小厮们也都若有所觉,暗地里有些发憷,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王爷惹人家恼了,又是八卦又是好奇。
唐三悄悄瞥了眼给他手臂扎着针的某人,眼看着那头的玉小刚给他使眼色,俊脸上颇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唐三垂眸盯着时影的侧颜微微失神,心尖愈发柔软
【这几日事毕,是得想法子哄哄人了....】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唐三连着上了四日朝,哪怕天气一日冷过一日,他也风雪不辍,日日都去议政殿。
坊间也不知谁开了头,从酒楼到街巷,从东坊传到了西坊,连普通老百姓都在议论,北境恐似又要再起战事,皇帝不仅不体恤归京遇刺受伤的镇北王,还让重病缠身的小王爷日日顶着风雪去上朝,没过几日,甚至都传出了镇北王在朝堂上失力昏迷,命不久矣的传言。
今上最是在乎脸面,那些传言愈演愈烈,眼看着第五日唐三又来上朝,脸色一日白过一日,哪怕特许了这人围着斗篷立在殿上,庆元帝也总觉这人瘦弱得像是一阵风吹过便要跌倒了一般。
皇帝面色极不好看,但他知道,这是唐三对他无声的表态。
那日,唐三首日上朝,哪怕是继任镇北王以来第一次,哪怕他除却北境兵权外在朝堂上孤立无援,但庆元帝仍是未曾从这人眼中看到哪怕一丝的退却。
果不其然,当日在议政殿上,皇帝虚伪的温和体恤才堪说完,群臣议事,没两句便入了正题,提到了北境边关有变,六百里加急塘报昨夜抵京,朝臣们像是刻意忽略了唐三的存在,大肆谩骂着蛮狄的暴行,仿佛痛心疾首一般,三五句过后,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图穷匕见,开始举荐起领兵的统帅人选。
然而,夷狄凶悍,如今又正值寒冬时节,北境如此苦寒艰险,十五万北境军更是唯镇北王唐三马首是瞻,旁人哪怕领了统帅之名,去了那里也是为唐三鱼肉,哪怕是垂涎战功,可临到了这等节骨眼,几乎所有人又都心生退却,他们心照不宣的,在朝堂上浅笑晏晏地客套,话语里句句是家国重于泰山,可话到最后,却仍是落到了沉默的镇北王身上。
庆元帝笑笑,面上苍老的痕迹掩藏不住,他像是很满意自己仁德的姿态,眼神分明居高临下,话音里却带上了乱真的赞赏:“看来,这次又要辛苦镇北王一趟,有镇北王为我天斗镇守北境,朕心甚慰啊!”
“是啊是啊!”
“有镇北王在,夷狄根本不足为惧啊...”
“没错,你看戎羯都已主动和谈,区区蛮狄又哪里翻得起什么风浪来....”
唐三第一次站在这座皇权至高的议政殿内,明明周身都是热烈议论的人潮,是天斗朝的中流砥柱,但听着他们的话语,他却只觉心寒,彻骨的寒凉好似跗骨之蛆自脊背攀遍全身,连同身体里蚀疼的旧伤疼痛一并袭来,他几乎要忍不住冷笑出声。
从头至尾,只言镇北王英勇,却只字未提他病骨支离,举步维艰;
从头至尾,只言北境军战无不克,却从不言十五万兵士食糙米,着单衣,出生入死,血流成河;
从头至尾,只言蛮狄粗野难驯,仿佛居高临下、颐气指使,将士百战死换来的胜利,却成了这些尸位素餐之人傲慢优越的凭借。
唐三第一次深切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恨的,是怨的,是不甘的,是愤怒的。
或许是这些年与皇城远隔千里,这些愤懑像是被积攒着,直到此时此刻,真正亲眼得见、亲耳听到,才将将爆发出来。
唐三朝四周环视一眼,不漏声色地对上北堂墨染深幽的视线,他读懂了对方眼底同样的嘲讽和冷意,很快偏过目光,再度望向皇位之上。
【墨染,如今看来,你的准备是对的。】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守住北境,哪怕.....】
心中百转千回,唐三俊脸上却始终古井无波,直到皇帝金口玉言定下了他统帅出征的旨意,他才有了反应,敛睫垂眸,哑声谢恩。
而接下来,议政殿内便十足的风起云涌,跌宕起伏。
那日,下了朝的百官全都噤若寒蝉,就连散朝时一个两个都走得飞快,没人敢多加停留,更没人胆敢随意结交一个皇帝心恶之人,何况唐三还手握重兵,因而那一日的议政殿,他一人走在了最后。
北堂墨染忧心他的状况,却碍于身份只能装作不识,缓步走在唐三前头领着。
但即便回了皇子府,他脑海中仍不断回旋着朝堂上唐三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恕臣直言,户部萧尚书年事已高,恐心力不足,前年筹措军备至今仍有军饷未厘清,北境军中多有兵士议论纷纷,为了军心安定,请陛下收回成命,再择人选为好。”
“陛下,臣自知忤逆陛下罪该万死,但北境一日不平,臣一日心有不安。”
“北境军备事关将士们是否能后顾无忧地冲锋陷阵,臣既领命出征,便不敢辜负陛下和将士们的期待。想陛下如此圣明仁德,绝不会让北境将士们寒心,请陛下三思!”
唐三从来都是年少早熟的,是极沉稳、极冷静的。
因而就连北堂墨染都没料到,唐三会当着庆元帝的面,如此直截了当地点出军备一事。
那日议政殿如此禀言,无异于忤逆圣颜,公然反驳了庆元帝的脸面。
但唐三却想得通透,他会如此激言当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朝中虽风气不佳,但据他与墨染了解,满朝文武里也还是有那么一些心系家国之人的,其中有许多还是当年与他父亲唐昊有旧的旧部。
更何况,皇帝虚情假意,对他早已起了杀心,他自然是无所谓是否失了帝心,是否被这位记恨,只要能有好结果,他已然无惧自己的安危。
哪怕过了数日,北堂墨染的眼前也历历在目——
年轻病弱的镇北王跪在地上,冰冷的玉石地板冷得渗人,但男人依旧背脊挺拔,不动不摇地跪着,垂眸拱手。
明明跪着,却像是仍铁骨铮铮地站在殿上一样。
最后的最后,皇帝借口身体不适,传旨退朝,此事便被搁置了。
如此,唐三上朝的首日,这场闹剧便被如此儿戏地截断了。
但唐三知道,北堂墨染也知道,不该说的话已经说了,有些事做了,那便只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正如唐三在议政殿所言,他既是北境军的统帅,是十五万将士信任的镇北王,那么他便要极尽所能地保护他们,战场刀枪无眼,他无法护得每一人周全,但他至少不能让他的士兵们因为朝堂上这些尸位素餐之人的贪婪和争斗失去性命。
于是,下了朝那天,回府的马车上,唐三与时影讲了此事。
时影被这人的胆大包天惊得瞠大了眼,但意识到唐三话里的言外之意,脸色却霎时黑沉了下去,“一鼓作气....你的意思是,你还要上朝?”
唐三抿唇,明明心中斟酌过无数遍,但同时影讲出来时,他却仍觉话音发虚:“是...是啊。”
“你知不知道,你体内的蓝银蛊尚未完全沉眠,随时都可能因你气血不稳而复苏!?”
“蓝银蛊苏醒根系植入血肉,痛不欲生,你的身体底子不好,随时可能熬不住一命呜呼,你明白吗?!”
唐三滚了滚喉结,瑞凤眸闪了闪,到底还是对上时影深幽的眼,他当然清楚自己的身体,也懂得眼前人眸中的忧虑,听着时影难得厉声说话,他却反倒安下心来,将自己身上的绒毯扯过些许,也盖在时影的膝上。
“阿影,你说的我明白,我自然不会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只不过,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皇帝今日的态度便是不想正面回应,但他深知我说的都是事实,以往我不在皇城,墨染不能暴露与我之间的关系,只能暗中相助,鞭长莫及,眼看着北境后方被他们拖累,如今我回来了,便只有我能做这件事。”
“可是.....”时影胸口闷疼,第一次有些止不住身体里的某股冲动,主动伸手覆上了唐三的手背。
白衣的医仙公子攥着掌下回暖的手,指节隐隐用力,他觉得喉咙涩得厉害,某句话到了嘴边,却就是不知如何开口。
“嗯?”
唐三看了看两人交叠的手掌,心尖一暖,正欲再说些什么,却听沉默许久的时影终于说话。
他的嗓音掺了喑哑的涩意,眼眶不可见地微红:“可是...这不公平。”
唐三闻言,唇角笑意一窒。
时影拧着眉,盯着唐三不挪眼,桃花眸里有纯然又执拗的神光,晃得唐三心乱。
“为什么又是你呢,这不公平。”
“并非你的过错,却要你用自己的身体来冒险?”
“怎么能说只有你呢?这并非你一个人的责任,不该全然由你来背负。”
时影咬牙,眼底有隐隐绰绰的泪光闪动,他到底才下山没多久,还未曾见识过太多狰狞和丑恶。
哪怕是面对病患的生离死别,他也能尽力冷静理智地劝解,可唯独唐三,他懂得他,他尊重他,他理解他,可他却无法说服自己。
时影想,他是一名医师,更自诩习得了师父的毕生所学,这些年也是救人无数。
但唯独唐三,他明明知道怎么救他,明明可以救他,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只能旁观,只能看着他做那些看似正确、看似果决的所谓选择,他不是不明事理,他只是无法说服自己,无法眼睁睁看着唐三将自己的性命,与北境的千千万万人放在一个天平上——这本身便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他也知道,唐三一定会选择对面,但他作为一名医师,却无法对任何一个宝贵的生命坐视不理。
更何况,这个人是唐三啊,是那么好那么好的唐三。
唐三从未想过,会有人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就好像从未想过,原来,除却身为“镇北王”,只身为“唐三”时,也有人如此在意他能不能好好活着。
一时之间,唐三有种冲动想要拥紧眼前人入怀,可一对上时影微红的眼眶,却霎时散去了旖旎,只余慌乱。
他慌了神,眼前骤然清明,赶忙撑起身来伸手去捧时影的脸,小心地抚了抚这人的眼尾,动作笨拙,声线却柔软得不可思议:“阿影....你别...别担心啊。”
“只是受点累,多上几天朝罢了,这几日过去了我就好好休养,不骗你!”
沉着冷静的镇北王手忙脚乱,裹紧了身上的绒毯和斗篷,他将自己围得像个软乎乎的绒球,拉着时影的手小心地哄他:“阿影你看,我挺好的,方才在朝堂上那般折腾,现在也好多了。”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是我遇见的最好的医师,以后也不会遇见你这么好的了。”
唐三从没哄过人,但胜在人够聪明,嘴也甜,像是无师自通一般,拉着时影不撒手,“我会听你的话,只要下了战场,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好好修养长命百岁的,好不好?”
在外顶天立地的镇北王语尾缱绻,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他实在长得俊美,时影被他凑得太近,难免脸热,“你...你要说话算话,我是你的医师,为了你的身体,你要听我的。”
唐三笑眯了眼,狭长的凤眸噙满了明亮的暖意,他百依百顺,赶忙点点头表态,满脸认真:“嗯,本王说话算数,一言九鼎。”
“你是我的医师,我都听你的。”
那日后,唐三好不容易哄好了时影,继续雷打不动地寅刻点卯去上朝,哪怕皇帝早就免了他一月早朝好好修养,他也每天都去。
时影自然也每日都陪着他,不仅陪着他上朝,下了朝也寸步不离,盯着他喝药,盯着他热敷,盯着他好好休息,唐三一开始还想劝他,后来见他坚持,便也只得放弃,怕时影光顾着照看他、不顾自己身体,赶忙差人在未央殿里腾了一处软榻,方便时影随时休憩。
镇北王上朝也没别的事,便是一再地重提军备筹措的问题。
皇帝以为唐三遇刺受伤,又有消息说他极度畏寒,当是无法再轻易上朝的。他只觉唐三到底也太年轻,仍是冲动莽撞得很,那日如此顶撞龙颜,加之冬日愈发寒凉,不论如何此人都不会如此不知好歹的,而只要军备筹措人选一事被按下,皇帝自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旧如过往那般纵容。
然而唐三却不如他愿,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一而再再而三,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每一日的镇北王皆是旧事重提,他像是料准了庆元帝还需依仗他对抗外族,也算准了临近整军出征的节骨眼,皇帝不敢寒了北境军士的心。
说来十足讽刺,正如唐三对时影所说的,唐三病弱的身体,在这个时刻反倒成了他的一道护身符。
皇帝无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位战功累累、病骨缠身的一品王爵施以任何惩戒,而眼看着唐三脸色愈发难看,坊间传闻更是愈演愈烈,甚至已经演化到了北境军分崩离析、边关将失、战火涂炭的地步。
五日时间,不仅是唐三一日日迫庆元帝妥协的时间;
更是北堂墨染暗中联通朝官的时间。
万幸,那座沉闷窒息的议政殿内,也并非所有人都甘愿沦为皇权贪欲的工具,还是有人在朝为官,服绯佩环,是为了一展宏图,为了家国兴旺,百姓安康,他们或许曾经沉默平庸,但稍作引导,却也能成为一股力量。
正也因此,一日胜过一日,唐三一再重提旧事,附议之人愈来愈多,皇帝只道是朝臣们也与他一般,不得不迫于坊间传闻的舆论,不得已站在了占理的那边,却没想过潜移默化间,一些事情便已然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阿影你知道吗?虽然我畏寒,但其实我并不讨厌冬日。”
“为何?”
“冬去春来,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总能等到春暖花开。”
“我只便等着,终可见万物复苏,生生不息。”
“阿影,北境的春其实很美,待这场仗打完了,我领你去看看。”
“好,一言为定。”